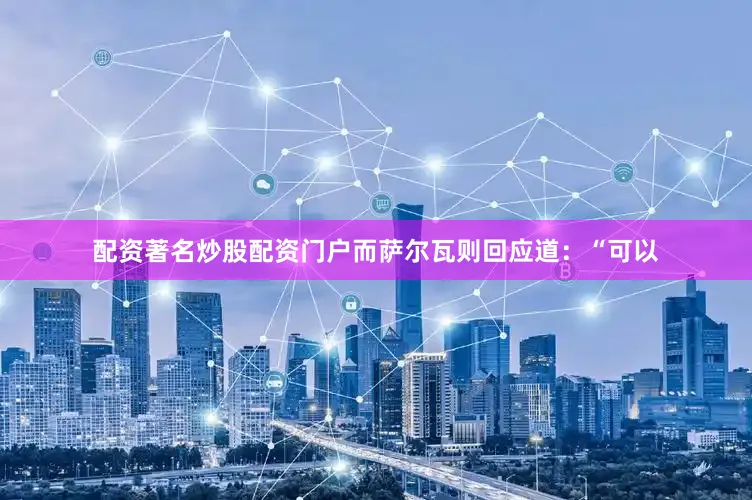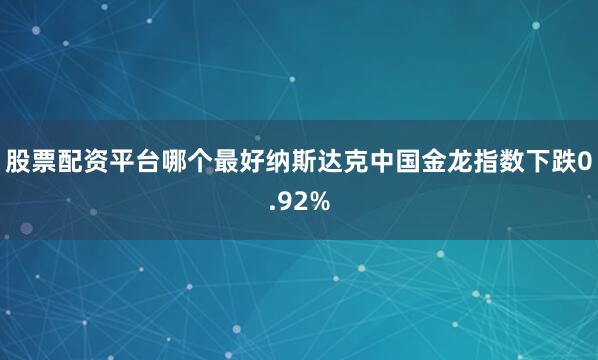书房闲坐,翻出半张发黄的信纸。铅笔字迹洇散模糊,唯有“活着,活着就是了”几个字,顽强地浮在纸面。台灯光晕微颤,空气里仿佛无声地悬着一道古老的命题。
这行字迹,是当年大学哲学课上,老师对“人为什么活着”提问的回应。对于这个问题,东西方先哲的答案林林总总,无非是驱散死亡的阴影、为生命寻找支点,但哲学老师这句朴素的话,偏偏有着诗歌般的“出人意料”。
对写诗的人来说,“出人意料”是诗歌的魂魄。这种“出人意料”或曰“新鲜感”并非刻意标新,而是在凝练的表达、情感的传递与意象的构建中,挣脱惯常逻辑的绳索,迸发出陌生化的美感和想象空间。诗歌因此得以跃出平铺直叙的牢笼,以更灵动、更具穿透力的方式,触碰感官和心灵。写诗,归根结底,或许就是在寻觅那些看似寻常、组合起来却充满颠覆力量的词语——它们如里尔克说的静默的树,只等一阵合适的风吹来,抖落沉睡的秘密。当词语携带过往烟尘与当下的生命体验相遇,那些被遗忘的意义,便被重新唤醒。
展开剩余88%八十年代末的一个秋日,我在故乡野地看到雨水泡软了一张马粪纸。它半陷泥中,边缘卷曲,隐约可见残留的字痕——或许是一个家庭柴米油盐的清单,或许是一封未曾投递或遭拒的情书。风吹过时,纸片窸窣作响,像草叶深处的低语。那个傍晚,我蹲在那里,直至暮色把我和纸片一起吞进黑暗。
后来,“马粪纸”这个词便走进我的诗里,如同那盏曾被我写进诗里的、执着于“寻找黑暗”的马灯。
彼时,我刚刚参加工作,栖身于济南洪家楼附近的一处办公楼里。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,单位买下了一家建筑公司的大院办公。诡异的是,楼道声控灯晚间常坏,夜半起行,需摸黑踩过三级松动的台阶。一日凌晨,划亮火柴,微光骤然照亮窗台——一盏建筑公司遗落的马灯,玻璃罩结满蛛网,灯芯早已烂作黑灰。就在那点摇曳的光里,我看见灯座上的“平安”二字,被岁月磨蚀得只剩淡痕,宛若两道未愈的伤口。
有时我会想,当年提着这盏马灯走在门前胶济铁路上的工人,铁轨反射的月光已足够明亮,他们是否也曾觉得这灯火是多余的累赘?恰如现在的我,面对满桌诗稿,忽而担忧词语的光芒过于刺眼,会照亮那些试图藏匿的秘密:文化东路上未说出口的歉意,英雄山月季花丛中被雨淋湿的背影,千佛山顶某个冬夜数过的星辰——每一颗都带着独特的疼痛。
有一年去呼伦贝尔草原旅游,与一位牧羊老人有过短暂交谈。他坐在羊群旁抽烟,烟锅里的火星明灭闪烁,像撒落草地的小小星辰。问他守着偌大天地是否孤单,老人指向远山,说:“孤单,是你还没找到愿意听你说话的石头。”那天晚上,躺在蒙古包里听风声穿过,不禁想起诗中写过的那句“每个怀乡者都握有一条马鞭”——原来诗人抽打记忆的姿态,与牧民驱赶牛羊并无二致。海德格尔说“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,这“诗意”并非文人的多愁善感,而是生命面对世界的本真回应:当一个诗人对石头开口,他已然站在了诗的源头。
诗的源头,自然也包括生死。
我写过一首《黑胶唱片》,纪念一位逝去的同事。早年居住在单位宿舍时,他常在洪楼西路的旧书摊淘碟,说唱片转动时的杂音是时间在呼吸。他走后,我找到一张他送我的未拆封的《伦敦德里小调》。此后每逢落雨,便播放这张唱片,看雨丝斜织窗棂,音乐里的爱尔兰草原,渐渐蔓生出济南的青苔。音乐在此刻消弭了终结,死亡以另一种形态,悄然渗入当下的生活。
最难忘的是写《车过临淄,想起一位死去的朋友》。当时,我坐在从潍坊回济南的火车上,飞驰的高铁窗外,高大的白杨如被时间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向后倾退。朋友S君是临淄某厂工人,原籍海阳,高中毕业后顶替父职入厂。因痴迷文学,与我有过多年书信来往。不幸的是,这位试图以文学改变命运的人,几年前被癌症带走。S君收入不高,平日却古道热肠、乐善好施,在厂里口碑极好。因属“少亡”,按当地风俗,遗体需要当天火化,但出殡那天,仍来了很多人。众人涕泪滂沱,相拥着哭成一片。我在疾驰的列车上写下此诗,不仅为倾吐未及言说的思念,更愿思念在诗中长成一片森林,为这个普通人立一块无字之碑。
常有读者问:你的诗,为何总萦绕着“不安”?
我想,除却对人生无常、世事难料的忧惧,或因目睹了太多事物的“裂痕”。在南山采石场,我见过炸药劈开的岩石断面,在阳光下泛着冷光,如大地裸露的骨头;在意大利北部小镇,我见过雨水泡烂的报纸,头版笑脸晕染成模糊的光斑;在自家阳台,昙花深夜绽放,花苞开裂之声恍若叹息,美得令人心碎。除此之外,人在囧途,更有命运不可捉摸的失落与遗憾让人猝不及防:时间单向奔流,蝴蝶效应翩然而至,让“圆满”成为稀世之珍。诗歌,恰是在这“无常”的生活中,捕捉生命最本真的脆弱与敬畏。克尔凯郭尔谓之“焦虑是自由的眩晕”,诗中的“不安”亦如是:它并非对存在的否定,而是人面对自身自由与有限性时必然的震颤。当惶惑沉淀,我们会发现——“不安”并非生命的缺陷,而是世界馈赠的一份粗砺的礼物。
2006年冬,黄河大坝树林里,我遇见一只白色的乌鸦。它羽毛白得泛蓝,立于光秃的榆树上啄食树胶。阳光穿透羽翼,洒落一地碎银。后来得知,这是因白化病被同类排斥的异类,只能在边缘地带孤独求生。但那天它昂首向天的姿态,毫无卑微,反似在冷眼睥睨整个世界的偏见,一脸不屑。
这个场景,后来被我写进《一只乌鸦在黄昏中暗自垂泪》。
写诗的人,大抵都是这样的乌鸦。
“诗人”这个名号,在当下语境里未必都是褒扬。譬如,在一些场合,主人在介绍我的身份时,往往还要特意加上一句“某某是诗人”,然后,其他人意味深长地跟着故作惊讶状:“咦——诗——人。”这时,未等大家“呵呵”,我已自惭形秽,忙说“别骂我”,恨不能立马钻到桌子底下。在现实生活中,诗人们身影游离,既渴望融入尘世喧嚣,又恐惧被磨平棱角、泯然众人。这种在入世与出世间的摇摆,常被视作“怪诞”。
有意思的是,我的诗歌也时常被人视作“怪诞”。收入集子中的那首《命中注定,我们要一起穿过黑暗》就是。诗中描述的是一次下夜班,与一位陌生女子默然同行于一条逼仄的小巷。那次偶遇,彼此无言,却仿佛能感知心跳的共振——一男一女,一前一后,以近乎亦步亦趋的节奏穿越黑暗。对黑暗的恐惧是人之本能,而相互依赖又相互提防,正是人在恐惧之下的本能选择。一个有共情能力的人,不难体会此中况味。在我看来,这恰恰孕育着一首好诗的胚芽。然而,令人苦笑不得的是,诗歌发布后,一位读者在后台留言,说这首诗歌通篇怪诞甚至荒诞,会把诗坛引到邪路上去。
好在我已习惯于把“怪诞”理解为风格。至于“邪路”,我告诉他,你高估了我和诗歌的胆量。
诗人韩东曾提出“诗到语言为止”,那么诗人呢?诗人是被语言选中者,受语言所托,他看守着那些语言无法言说的秘密。如果说诗歌是有使命的,那么,它也只能在“可说”与“不可说”的边界上踽踽独行。
去年整理旧稿,翻出八十年代校园里写的第一首诗。那时痴迷文学,常怀抱诗稿穿梭于宿舍、教室、图书馆之间。某日雨中路过小树林,诗稿淋湿,墨迹晕染成一片忧伤的蓝。心疼之余,在空白处写下:“孤独的小手,它能抓住潮湿的时光吗?”这首题为《孤独之手》的小诗不久刊登于系刊《驼铃》上。如今再看,将雨丝比作“小手”未必靠谱,但指尖仿佛仍能触到纸页未干的水渍,鼻尖似又嗅到当时空气里的土腥——原来所有词语皆是时光撒落的盐粒,在岁月里慢慢腌渍出滋味。
这本诗集分为三辑:
辑一:不是所有的乌鸦都身披黑暗。此辑多关乎过往记忆、自然物象与复杂的人生况味。有对特定年代的回望,如《八十年代》中与同学夜车畅谈的青涩;亦有对自然事物的另类凝视,如《不是所有的乌鸦都身披黑暗》,试图打破“乌鸦即黑暗”的窠臼,指向事物本有的多面;孤独、不安、悲伤如影随形,《不安之美》道出对美好事物的隐秘悸动;《悲伤的人是有福的》则在哀恸深处挖掘过往的刻痕与生命的重量。
辑二:午夜火车。此辑偏重亲情牵绊、自我省察、生死顿悟与时光旅途。《母亲节》流淌对母亲的追念,《妹妹,今夜我已羞于赞美》蕴含复杂的情感羁绊;《面对大海,我常常感到卑微而胆怯》是对自身渺小的体认;《墓志铭》则是对生命终点的想象与叩问。
辑三:一只马灯在寻找黑暗。此辑沉潜于孤独与隐秘的探索,以及与自然生灵的对话和对存在意义的沉思。《一只马灯在寻找黑暗》以灯为喻,主动追寻“黑暗”(隐秘、孤独)的真相;《与一只英短蓝猫对视》借猫的眼神,映照人与万物的情感连接;《一想到这一生寂寂无名,我就心花怒放》在平凡中觅得坦然;《扎羊角辫的师妹,兼致海子》则交织着对青春过往与诗坛先辈的幽深怀念。
细读下来,你会发觉,诗集中没有宏大的叙事,有的只是个体经验、生命轨迹和感官记忆——我称之为“个人史写作”。在波澜壮阔的集体记忆之下,正是无数个体的日常烟火、幽微情愫与私人体验,织就了历史最鲜活的肌理。个人史写作以个体生命为刻度,用文字打捞那些被宏大叙事遗忘的尘埃,让每个普通人成为自身生命的历史学家。它们如同撒落一地的拼图碎片,单看只是微小的色块,拼接起来,便是一个人的心灵地图或成长编年。“诗歌是穿越存在废墟的闪电”,而这些碎片的聚合,或许正等待着成为那道闪电——它无意照亮所有角落,只求在某个瞬间,让生活的轮廓在黑暗中骤然显现。另外,在写作中,我时刻警惕将个人史写成一份“成绩清单”。窃以为,与那些甜美的自我粉饰相比,失败的尝试、隐秘的憾恨,甚至看似无意义的日常,往往更能引发普遍的共鸣——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里,都藏着相似的迷茫与平凡。
有次在咖啡馆与朋友闲坐,灵感忽至,急寻纸片记下。他见我涂涂改改,笑言:“伙计,写完就别轻易再动了。”我答:“好诗是改出来的。”其实这些年涂改删削的,何止词语,还有身上那些曾自以为锋利的棱角——如同将顽石置入溪流,任时光磨去它的嶙峋,只留下最温润的质地。多年写作经验告诉我,诗的意义并非一蹴而就,它在反复的修改与重读中,如植物般缓慢生长。诗人修改诗稿,本质上是在与词语、与自身、与过往进行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。
去年冬日归乡,见院中老槐树被大风折断枝桠,断口处渗出琥珀色的汁液。我蹲踞树下锯断残枝,木屑纷飞间,蓦然想起诗人树才翻译的安让·阿尔托诗句:“它居住在阴影沉甸甸的心中/一颗心破裂,一颗坚硬地分成两半。”那天午后,我坐在树墩上晒太阳,看槐树的汁液在阳光下渐渐凝固成痂,忽然彻悟:写诗,不就是为那些深埋地底的根系,刨开一条得以呼吸的通道么?
我深信诗歌的诞生如同地壳运动。那些嵌于岩层中的贝壳化石,千万年前曾在潮汐中开合,如今成了石头内部恒久的心跳。《不安之美》中的诗歌亦是如此,它们最初只是散落的碎片,在笔记本中沉睡经年。直至某个雪夜,我发现它们开始彼此吸引,如同磁石吸附铁屑,渐渐拼出一条微光闪烁的小径。诗的本质,或许正是这种“地质性”的沉淀与爆发——赋予瞬间感受以磐石般的重量,将私密记忆淬炼为人类的共同记忆。
需要强调的是,“不安”从来不是诗歌的敌人。它恰似钟摆的律动,因了这往复的摇摆,时间才拥有了韵律。《钟摆飘荡》中写的“一个早起的人开始出发 / 准确到以分秒计 / 在钟摆的飘荡中 / 穷人赶路,富人慵懒 / 中产阶级探讨意义”——道出的正是这种永恒的时差。诗歌所能捕捉的,是人在追赶途中的喘息与回望:它无力消除不安,却能让不安本身,成为照亮生活幽微处的光。
我愿意将这些诗篇献给所有在夜色中擎起灯火的人,献给所有于窒息处奋力呼吸的灵魂。倘若某个瞬间,你在这些句子中瞥见了自己的影子,那一定是风,将我们各自的回响,吹送到了同一个角落。
毕竟,万物都在寻找自己的共鸣。就像那盏马灯,终会在最深的黑暗里,遇见懂得它的眼睛。
(摄影:Andrew Mohrer)
发布于:山东省满盈网配资-配资合作网-股票配资开户-股票配资导航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